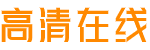曾經的Stellantis集團,在中國市場的姿態更像一個謹慎的旁觀者,甚至一度被外界解讀為“準備離場”,其前任CEO唐唯實還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對中國市場激烈競爭和獨特游戲規則的“不適應”,再加上在華合資公司廣汽菲克的黯然離場,以及神龍汽車的持續低迷,都讓業界普遍認為,這家由PSA與FCA合并而成的全球汽車巨頭,正在逐步降低其在中國這一全球最大汽車市場的權重。
然而,最近兩三年間,我們能夠明顯感受到,Stellantis的中國戰略可謂是畫風驟變,一系列密集且深入的合作協議,持續扭轉著外界的觀感。
從斥資十數億歐元入股零跑汽車并組建合資公司,到與東風集團達成全面深化合作、將神龍汽車體系融入東風新能源事業版圖,再到攜手小馬智行推進L4級自動駕駛商業化等,Stellantis這家外資車企,近年來可謂是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中國粘性”。

圖片來源:Stellantis
從“水土不服”到“生態融入”
Stellantis與中國市場相關的一系列的動作,顯然都不是孤立的商業行為,而是其中國戰略正在經歷的一場根本性的、系統性的重塑。Stellantis正在放棄過去那種試圖以全球標準化產品征服中國市場的傲慢,轉而以外資車企此前在華少見的謙遜與務實態度,尋求深度嵌入中國汽車產業創新生態的可能性,試圖從內部尋找破解中國市場困局的密碼。
這一轉變,不僅關乎Stellantis自身的存亡,更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所有外資汽車品牌在中國這個全球最卷,同時也是當前最前沿的汽車產業賽道上,所必須要面對的殘酷現實。換言之,Stellantis的態度轉變,并非一時興起的決策,而是內外壓力交織之下,綜合權衡了利弊之后的必然選擇。
背后的驅動力量,既有對中國市場殘酷競爭現實的重新審視,也有對全球戰略資源重新配置的需求。
在唐唯實時代,Stellantis對中國市場的批評表面看主要集中于政策環境的公平性及在華業務盈利能力等方面,但其實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其賴以生存的傳統燃油車業務與合資模式,在中國市場已經失去“魔力”。
廣汽菲克因產品迭代緩慢、品控問題頻發,最終以破產清算告終。
神龍汽車(旗下含東風標致、東風雪鐵龍)雖有過短暫復蘇,但在國內的新能源轉型浪潮中,也已經再次掉隊,銷量長期在低位徘徊,其在華整體市場份額已經嚴重萎縮,邊緣化危機迫在眉睫。
究其原因,電動化轉型嚴重滯后是關鍵,盡管Stellantis在歐洲市場的電動化表現強勁,但其前期導入中國的純電車型如標致e-2008等,或因“油改電”平臺技術落后,或因定價策略失當,均未能在激烈的中國市場競爭中激起任何水花。與中國品牌層出不窮、迭代迅速的智能電動車產品相比,其產品力存在代際差。
這一切的根源,在于過去“外方輸出車型、中方負責本土化與渠道”的傳統合資模式,在智能電動車的快節奏競爭中已顯得笨重且低效。決策鏈條過長、對中國消費者需求的響應速度慢、核心技術(尤其是智能座艙與輔助駕駛系統等)的本地化適配不足,成為致命的短板。
面對困局,Stellantis沒有放棄,還在積極的通過一系列新的嘗試,這其中,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轉換經營思路,核心就是從主導者轉變為參與者和賦能者。
入股零跑,是以資本換取技術與時間的嘗試。出資15億歐元獲取零跑汽車20%左右的股權,還和零跑汽車一起成立了零跑國際合資公司,在國內汽車市場上,Stellantis和零跑的這次合作,堪稱是有戰略意義的一次標志性事件。
此舉意圖非常明確:對零跑汽車而言,可以借力Stellantis的全球資源加速國際化進程,對Stellantis而言,也可以借助零跑汽車的創新意識和優秀的成本效益,完成電動車生態的搭建,加速電氣化的企業轉型。“零跑國際”合資公司主攻中國以外的全球市場,Stellantis可以利用其遍布全球的制造基地和成熟的銷售網絡,為零跑車型的出海鋪平道路,當然,這一過程中,Stellantis自身也能從中獲利,雙方的合作,可以實現典型的以內促外、以外補內的協同效果。

圖片來源:零跑汽車
此外,入股零跑汽車,對Stellantis而言,也意味著可以獲得現成的新能源技術平臺。零跑自研的“四葉草”中央集成式電子電氣架構及其整車平臺,是當前行業領先的技術方案之一,Stellantis通過投資,可以直接獲得這些核心技術的使用權和共同開發權,將極大的縮短其自身平臺的研發周期。而且借助零跑的本土供應鏈,Stellantis在合作的過程中,還能更好的降本增效,零跑汽車的背后是中國成熟且極具成本優勢的新能源汽車供應鏈體系,Stellantis可利用此體系,為其全球其他市場開發更具價格競爭力的電動車型。
與此同時,雖然神龍汽車近年來的市場表現不溫不火,但Stellantis還是在繼續深化與東風的合作。對Stellantis而言,與零跑的合作是增量拓展,而與東風的深化合作同樣重要,畢竟這些已經投資數十年的資產,如果能再次“盤活”,也是核心“戰役”的勝利。
那么,究竟要如何去盤活呢?
首先肯定要與過往的模式劃清界限,神龍汽車現在在做的是“融入式”轉型。目前Stellantis已經與東風達成協議,將雙方的合資公司神龍汽車,融入到了東風的新能源事業版圖中。此舉不僅能為Stellantis甩掉沉重的產能包袱,甚至還能將其轉化為潛在的利潤中心。
此外,Stellantis還將“借用”東風的新能源平臺,為中國市場乃至全球市場打造全新的電動車型。此前,神龍汽車融入東風新能源事業版圖戰略已經落地,正式發布了自主新能源汽車品牌示界,首款車型示界06也已經官宣上市,定位為緊湊型純電SUV,神龍汽車也算是正式開啟合資車企轉型的新模式。Stellantis在中國市場暫時放下了技術輸出者的角色,轉而成為技術引入者,以求能夠更快的填補自身新能源產品的空白。
而這一系列操作之后,Stellantis與東風這一重要伙伴的關系不僅得以鞏固,避免了廣汽菲克式的不歡而散,而且還為未來可能的更深層次合作保留了可能性。
此外,Stellantis還與國內智駕領域的頭部玩家之一小馬智行達成了深度合作。10月17日,Stellantis集團和小馬智行共同宣布,雙方已簽署一份不具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旨在加速自動駕駛車輛解決方案在歐洲的開發和部署,據悉雙方將共同開發和測試L4級自動駕駛車輛,并將Stellantis的AV-Ready平臺與小馬智行的自動駕駛技術相結合。在自動駕駛領域,尤其是在L4級高階智駕方面,中國的不少科技企業已經處于全球第一梯隊。Stellantis與小馬智行的合作,不僅是一次商務投資,更是一次技術“補課”,通過與本土頂尖玩家的合作,快速理解并掌握適用于復雜路況的自動駕駛技術,并將其反哺至全球產品線,對Stellantis而言,無疑也是走上了一條加速智能化轉型的快車道。
綜合而言,Stellantis近期與中國相關的系列動作,可以概括為放下身段,以資本為紐帶,深度嵌入中國最具活力的智能電動車產業生態。它不再試圖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中國市場的洪流,而是選擇成為生態中的一環,想要通過資源互換與優勢互補,實現自身在全球競爭中的利益最大化。

圖片來源:Stellantis
Stellantis的轉變是當前汽車業的范式革命?
Stellantis當前的戰略轉向,其意義不僅是一家外資車企的個體行為,也標志著中國汽車產業在經過數十年的“市場換技術”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并將引發一系列深遠的行業連鎖反應。
首先肯定是“技術逆差”時代的正式開啟。
過去數十年間,中國汽車產業的主流一直都是“技術引進”,外資品牌憑借先進的發動機、變速箱技術和品牌優勢,占據價值鏈頂端。
此前的Stellantis在華業務雖然距離頂流合資車企陣營還有一段距離,但巔峰時期也曾是歐系車中不可忽視的主流勢力,現在Stellantis反向采用中國車企(零跑、東風等)的電動平臺和技術,這一“技術逆流”現象,在整個行業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也宣告了,在智能電動車這個全新的賽道上,中國在產業鏈完整性、技術迭代速度和成本控制等方面,已經形成了結構性的優勢且短期內已經很難被逾越,外資品牌想要在中國市場生存,就必須在技術上“向東看”。
當然,尤其是所謂的合資模式,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也就是當前不少主流合資車企都在重點關注的合資2.0時代。
什么是合資2.0?簡單而言,就是從單純的“合資”,升級為了“合智”和“合姿”。
Stellantis的案例為“新合資時代”提供了清晰的藍圖。未來的中外合作,將不再是簡單的品牌授權和生產合作,而是深入到資本、技術、供應鏈和全球市場的全方位融合。
技術層面,中外雙方合作研發、技術雙向授權或將成為主要內容。中方將首次在技術輸出端扮演重要角色,合作開發的產品不僅服務于中國市場,也將面向全球,這就是所謂的合智。
從資本層面,交叉持股或將成為常態。外資通過投資中國有潛力的科技公司或新勢力,快速獲取技術和市場洞察;而中國車企也可以通過資本紐帶,加速其全球化布局。而這就是所謂的合姿。
合作模式變了,分工肯定也將調整,可以預見,未來的合資企業中,中外勢力的分工將更加專業化。中方可能更側重于軟件、智能座艙、本地化應用和供應鏈管理;外方則可能憑借其全球品牌影響力、大規模制造經驗和海外渠道網絡等,去主導全球市場的開拓與運營。
這種新模式的核心,其實就是從零和博弈轉向共生共贏,共同應對全球汽車產業的大變局時代。
更重要的是,中國將成為全球汽車技術的策源地和試驗場。
Stellantis將與零跑、小馬智行等展開合作,大眾也已經與小鵬有股權上的合作,還與越來越多的中國科技企業有了合作成果,這實質上就是將中國市場驗證過的成功技術、產品和商業模式,進行全球化復制的過程。很顯然,現階段的中國不再僅僅是全球最大的汽車銷售市場,更升級為全球汽車產業,特別是智能電動領域的技術創新策源地和商業模式的試驗場。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外資品牌將其在中國的研發中心升級為全球研發樞紐,專注于智能網聯、自動駕駛等前沿技術的開發,而這些,都將在新的汽車轉型時代,塑造出中國勢力無可替代的硬實力和江湖地位。
外資品牌群體的中國突圍之道
Stellantis等企業的轉型,其實也為所有在華外資汽車品牌提供了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樣本,在競爭已呈“紅海”態勢的中國市場,固守舊有模式無異于坐以待斃。每一家外資品牌都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中國戰略,尋找新的定位和生存法則。
當前合資車企作為整體,處境都不太妙,絕大多數品牌都在共同經歷著市場份額、技術迭代和決策效率之困。
在一眾本土巨頭和“蔚小理”等新勢力的擠壓下,包括曾經風光無限的BBA等豪華品牌在內,主流外資品牌目前在國內市場上的份額都在持續下滑,品牌溢價能力減弱。此外,在智能座艙的流暢度、人機交互的智能化水平、輔助駕駛功能的用戶體驗上,外資產品與中國品牌之間也存在明顯的代差,在軟件定義汽車的時代,傳統的機械工程師文化正面臨著巨大挑戰。而且傳統外資車企此前遵循的全球一體化戰略,與快速變化的中國市場需求之間也是矛盾不小,一款全球車型從提出本土化修改建議到最終落地,周期漫長,往往就錯過了市場窗口。
面對挑戰,外資品牌的前景也已經出現顯著分化。有積極布局的,開始果斷地調整戰略,以靈活、開放的態度與中國產業生態深度融合,這樣的品牌,還保留著重獲生機的可能性,它們可能不再追求銷量上的絕對領先,而是通過在特定細分市場(如借助本土技術的電動化產品、或堅持自身特色的高端燃油車)的精耕細作,找到可持續的盈利模式。也有艱難的追隨者,部分品牌已經陷入“想變又不敢大變”的困境,試圖通過加大本土研發投入、加快產品導入速度來追趕,但其轉型步伐若跟不上市場變化的速度,將長期處于被動防守和利潤攤薄的境地。當然,未來肯定也少不了被邊緣化的退出者,那些品牌勢弱、技術儲備不足、且戰略猶豫不決的二三線外資品牌,很可能步廣汽菲克的后塵,最終被中國市場淘汰。
從當前的市場行情看,想要成為成功的轉型者,外資品牌必須進行一場從思想到行動的深刻變革。
戰略層面,要逐步放棄所謂全球車的幻想,踐行“在中國,為中國”的深度本土化。這不僅意味著產品的本土化適配,更包括研發、采購、決策乃至企業文化的本土化。要賦予中國區更大的自主權,建立能夠快速響應中國市場需求的研發和決策體系。
技術層面,也需要更加靈活,拿來主義還是自主開發,可以從實際條件出發靈活決策,對于自身短板明顯且追趕成本高昂的領域(如智能座艙、智駕平臺),應毫不猶豫地通過投資、合作或技術授權的方式,引入中國頂尖供應商或車企的解決方案。同時,集中資源鞏固自身在品牌調性、底盤調校、全球化設計等方面的傳統優勢。
此外,在合作層面,需要進一步拓寬伙伴邊界,構建“價值共生”生態圈。合作伙伴不應再局限于傳統整車廠,而應積極擁抱科技公司、頭部供應商、甚至出行服務商。通過組建戰略聯盟、成立合資公司、交叉持股等多種形式,構建一個以自身為核心的、開放的價值網絡。
當然,還有很核心的一點,要做好新的角色定位,其中國業務的核心使命可能需要重新定義:從利潤中心和銷售市場,轉變為技術前沿哨、創新孵化器和全球供應鏈優化樞紐等,都是利用中國的創新速度和成本優勢,反哺全球業務的不錯選項。
小結:Stellantis的在華大轉向,是一場被危機逼出的先行者的自救,更是一次順應時代潮流的智慧選擇。它深刻地揭示了一個事實,在智能電動化的新紀元,沒有任何一家企業(無論其歷史多么輝煌、規模多么龐大),都不可能僅憑一己之力通吃全球市場。尤其是在中國這個已經完成市場教育和產業鏈超強整合的市場,合作與融合是唯一的選擇。
這場變革對于中國汽車產業而言,是本土技術創新能力得到全球認可的明證。對于全球汽車產業而言,則預示著一個更加開放、多元、協同的新競爭格局正在形成。未來的贏家,不再是那些擁有雄厚歷史積淀或龐大銷量的巨頭,而是那些具備學習能力,懂開放協作,能快速適應生態演變的“新物種”。